译文及注释
译文
久久滞留在远离家乡的地方,依依不舍地向往着春天的景物。
寒梅最让人遗恨的是早占春意却又早早凋谢,常常被称为“去年花”。
注释
定定:唐时俗语,类今之“牢牢”。
天涯:此指远离家乡的地方,即梓州。
物华:万物升华,指春天的景物。
寒梅:早梅,多于严冬开放。
恨:怅恨,遗憾。
去年花:指早梅。因为梅花在严冬开放,春天的时候梅花已经凋谢,所以称为“去年花”。
鉴赏
这是李商隐作幕梓州后期之作,为咏梅而寓意之诗。写在百花争艳的春天,寒梅早已开过,所以题为“忆梅”。
一开始诗人的思绪并不在梅花上面,则是为留滞异乡而苦。梓州(州治在今四川三台)离长安一千八百余里,以唐代疆域之辽阔而竟称“天涯”,与其说是地理上的,不如说是心理上的。李商隐是在仕途抑塞、妻子去世的情况下应柳仲郢之辟,来到梓州的。独居异乡,寄迹幕府,已自感到孤孑苦闷,想不到竟一住数年,意绪之无聊郁闷更可想而知。“定定住天涯”,就是这个痛苦灵魂的心声。定定,犹“死死地”、“牢牢地”,诗人感到自己竟象是永远地被钉死在这异乡的土地上了。这里,有强烈的苦闷,有难以名状的厌烦,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哀。屈复说:“‘定定’字俚语入诗却雅。”这个“雅”,似乎可以理解为富于艺术表现力。
为思乡之情、留滞之悲所苦的诗人,精神上不能不寻找慰藉,于是转出第二句:“依依向物华。”物华,指眼前美好的春天景物。依依,形容面对美好春色时亲切留连的意绪。诗人在百花争艳的春色面前似乎暂时得到了安慰,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对美好事物无限依恋的柔情。一、二两句,感情似乎截然相反,实际上“依依向物华”之情即因“定定住天涯”而生,两种相反的感情却是相通的。
“寒梅最堪恨,长作去年花。”三、四两句,诗境又出现更大的转折。面对姹紫嫣红的“物华”,诗人不禁想到了梅花。它先春而开,到百花盛开时,却早花凋香尽,诗人遗憾之余,便不免对它怨恨起来了。由“向物华”而忆梅,这是一层曲折;由忆梅而恨梅,这又是一层曲折。“恨”正是“忆”的发展与深化,正像深切期待的失望会转化为怨恨一样。
但这只是一般人的心理。对于李商隐来说,却有更内在的原因。“寒梅”先春而开、望春而凋的特点,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:少年早慧,文名早著,科第早登;然而紧接着便是一系列不幸和打击,到入川以后,已经是“克意事佛,方愿打钟扫地,为清凉山行者”(《樊南乙集序》),意绪颇为颓唐了。这早秀先凋,不能与百花共享春天温暖的“寒梅”,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。诗人在《十一月中旬扶风界风梅花》诗中,也曾发出同样的感叹:“为谁成早秀?不待作年芳。”非时而早秀,“不待作年芳”的早梅,和“长作去年花”的“寒梅”,都是诗人不幸身世的象征。正因为看到或想到它,就会触动早秀先凋的身世之悲,诗人自然不免要发出“寒梅最堪恨”的怨嗟了。诗写到这里,黯然而收,透出一种不言而神伤的情调。
五言绝句,贵天然浑成,一意贯串,忌刻意雕镂,枝蔓曲折。这首《忆梅》,“意极曲折”(纪昀评语),却并不给人以散漫破碎、雕琢伤真之感,关键在于层层转折都离不开诗人沉沦羁泊的身世。这样,才能潜气内转,在曲折中见浑成,在繁多中见统一,达到有神无迹的境界。▲
鉴赏二
这是李商隐作幕梓州(治今四川三台)后期之作。写在百花争艳的春天,寒梅早已开过,所以题为“忆梅”。
“定定住天涯,依依向物华。”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,滞留在远离家乡的地方,依依不舍的向往着春天的景物。“定定住天涯”,可看得出一开始诗人的思绪并不在梅花上面,而是因为滞留异乡而苦。梓州(今四川三台)离长安一千八百余里,以唐代疆域之辽阔而竟称“天涯”,与其说是地理上的,不如说是心理上的。李商隐是在仕途抑塞、妻子去世的情况下应柳仲郢之辟,来到梓州的。独居异乡,寄迹幕府,已自感到孤孑苦闷,想不到竟一住数年,意绪之无聊郁闷更可想而知。这句就是这个痛苦灵魂的心声。定定即是“死死地”、“牢牢地”,诗人感到自己竟象是永远地被钉死在这异乡的土地上了。这里,有强烈的苦闷,有难以名状的厌烦,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哀。屈复评此句说:“‘定定’字俚语入诗却雅。”这个“雅”,似乎可以理解为富于艺术表现力。
为了克服思乡之情,留滞之悲所苦的诗人,精神上不能不寻找慰藉,于是就有了第二句的转折:“依依向物华”。“物华”,指眼前美好的春天景物。“依依”形容面对美好春色时亲切留恋的情绪。诗人在百花争艳的春色面前似乎暂时得到了安慰,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无限依恋的柔情,一、二两句,感情似乎截然相反,实际上“依依向物华”是因为“定定住天涯”而生,两种相反的感情是具有因果关系的。
“寒梅最堪恨,常作去年花。”小诗的后两句是说,寒梅最能惹起人们的怨恨,因为老是当作去年开的花。
三四两句,诗景又出现更大的转折。面对姹紫嫣红的“物华”,使人不禁想起了梅花。它先春而开,到百花盛开时,却早已花凋香尽,诗人遗憾之余,便不免对它怨恨起来了。由“向物华”而想到梅花,,这是一层曲折,由想到梅花而怨恨梅花,这又是一层曲折。“恨”正是“忆”的发展与深化。正像深切期待的失望会转化为怨恨一样。
李商隐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呢,是有着更内在的原因的,“寒梅”先春而开,望春而凋的特点,使诗人很自然的联想到自己:少年早慧,文名早著,科第早登;然而紧接着一连串不幸和打击,到入川以后,已经是少年壮志成浮云,意绪颇为颓唐了,这早朽先凋,不能与百花共享春天温暖的“寒梅”,不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吗?正因为如此,看到和想到它,就会触动内心深处的早秀先凋的身世之感,诗人自然不免要发出“寒梅最堪恨”的嗟叹了。
这首《忆梅》,意极曲折,却并不给人以散漫破碎、雕琢伤真之感,关键在于层层转折都离不开诗人沉沦羁泊的身世。这样一来,便显得此诗潜气内转,在曲折中见浑成,在繁多中见统一,达到有神无迹的境界。▲
创作背景
这首诗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。只知道是其作幕梓州后期之作,此诗写在百花争艳的春天,在作诗之时寒梅早已开过,所以题为“忆梅”。
简析
《忆梅》是一首五言绝句。此诗通过描写春日游玩而不见梅花这件事,表达诗人因怀才不遇、流离辗转而生发愤懑颓唐的思想感情。全诗浑然天成,一意贯串,并无刻意雕镂,枝蔓曲折,显得潜气内转,在曲折中见浑成,在繁多中见统一,达到有神无迹的境界。
李商隐(约813年-约858年),字义山,号玉溪(谿)生、樊南生,唐代著名诗人,祖籍河内(今河南省焦作市)沁阳,出生于郑州荥阳。他擅长诗歌写作,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,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,和杜牧合称“小李杜”,与温庭筠合称为“温李”,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、温庭筠风格相近,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,故并称为“三十六体”。其诗构思新奇,风格秾丽,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,优美动人,广为传诵。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,难于索解,至有“诗家总爱西昆好,独恨无人作郑笺”之说。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,一生很不得志。死后葬于家乡沁阳(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)。作品收录为《李义山诗集》。
苏秦始将连横,说秦惠王曰:“大王之国,西有巴、蜀、汉中之利,北有胡貉、代马之用,南有巫山、黔中之限,东有肴、函之固。田肥美,民殷富,战车万乘,奋击百万,沃野千里,蓄积饶多,地势形便,此所谓天府,天下之雄国也。以大王之贤,士民之众,车骑之用,兵法之教,可以并诸侯,吞天下,称帝而治。愿大王少留意,臣请奏其效。”
秦王曰:“寡人闻之:毛羽不丰满者,不可以高飞,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,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,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。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,愿以异日。”
苏秦曰:“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。昔者神农伐补遂,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,尧伐驩兜,舜伐三苗,禹伐共工,汤伐有夏,文王伐崇,武王伐纣,齐桓任战而伯天下。由此观之,恶有不战者乎?古者使车毂击驰,言语相结,天下为一,约从连横,兵革不藏。文士并饬,诸侯乱惑,万端俱起,不可胜理。科条既备,民多伪态,书策稠浊,百姓不足。上下相愁,民无所聊,明言章理,兵甲愈起。辩言伟服,战攻不息,繁称文辞,天下不治。舌弊耳聋,不见成功,行义约信,天下不亲。于是乃废文任武,厚养死士,缀甲厉兵,效胜于战场。夫徒处而致利,安坐而广地,虽古五帝三王五伯,明主贤君,常欲坐而致之,其势不能。故以战续之,宽则两军相攻,迫则杖戟相橦,然后可建大功。是故兵胜于外,义强于内,威立于上,民服于下。今欲并天下,凌万乘,诎敌国,制海内,子元元,臣诸侯,非兵不可。今之嗣主,忽于至道,皆惛于教,乱于治,迷于言,惑于语,沉于辩,溺于辞。以此论之,王固不能行也。”
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,黑貂之裘敝,黄金百斤尽,资用乏绝,去秦而归,羸縢履蹻,负书担橐,形容枯槁,面目犁黑,状有愧色。归至家,妻不下紝,嫂不为炊。父母不与言。苏秦喟叹曰:“妻不以我为夫,嫂不以我为叔,父母不以我为子,是皆秦之罪也。”乃夜发书,陈箧数十,得太公阴符之谋,伏而诵之,简练以为揣摩。读书欲睡,引锥自刺其股,血流至足,曰:“安有说人主,不能出其金玉锦绣,取卿相之尊者乎?”期年,揣摩成,曰:“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。”
于是乃摩燕乌集阙,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,抵掌而谈,赵王大悦,封为武安君。受相印,革车百乘,锦绣千纯,白璧百双,黄金万溢,以随其后,约从散横以抑强秦,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。
当此之时,天下之大,万民之众,王侯之威,谋臣之权,皆欲决苏秦之策。不费斗粮,未烦一兵,未战一士,未绝一弦,未折一矢,诸侯相亲,贤于兄弟。夫贤人在而天下服,一人用而天下从,故曰:式于政不式于勇;式于廊庙之内,不式于四境之外。当秦之隆,黄金万溢为用,转毂连骑,炫熿于道,山东之国从风而服,使赵大重。且夫苏秦,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,伏轼撙衔,横历天下,廷说诸侯之王,杜左右之口,天下莫之能伉。
将说楚王,路过洛阳,父母闻之,清宫除道,张乐设饮,郊迎三十里。妻侧目而视,倾耳而听。嫂蛇行匍伏,四拜自跪而谢。苏秦曰:“嫂何前倨而后卑也?”嫂曰:“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。”苏秦曰:“嗟乎!贫穷则父母不子,富贵则亲戚畏惧。人生世上,势位富贵,盖可忽乎哉?”
 李商隐
李商隐 岳岱
岳岱 梅尧臣
梅尧臣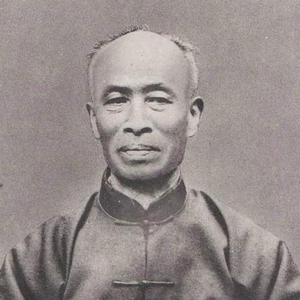 郑孝胥
郑孝胥 杨万里
杨万里 杨亿
杨亿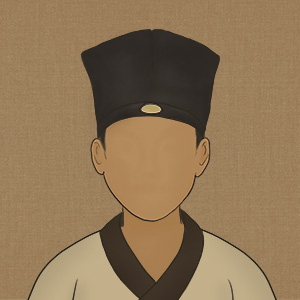 乌斯道
乌斯道 戴复古
戴复古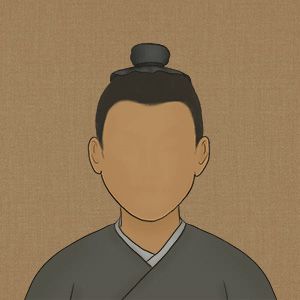 战国策
战国策 廖行之
廖行之